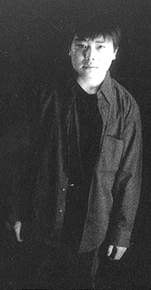老男人也有春天
老男人也有春天

“當人類發現每個人都那么危險的時候,惟一的辦法就是大家要彼此信任,每個人都要更努力。人是我們惟一可以相信的共同體,難道你要相信空氣嗎?相信海水嗎?相信動物嗎?”圖本刊記者 大食
 2004年5月6日,羅大佑和神祕嘉賓潘越云及齊豫合影
2004年5月6日,羅大佑和神祕嘉賓潘越云及齊豫合影
 羅大佑和李宗盛等在一起
羅大佑和李宗盛等在一起 羅大佑 所有情感和觀點都在音符里
本刊編輯部
羅大佑、李宗盛、周華健、張震岳,這4位在華語樂壇的分量是令人震驚的:總共發行70張個人專輯,發表近600首作品,爆滿過350場個唱……也只有這4位唱將組成的樂隊,才敢自稱super band(超級樂隊)。
2009年的春晚,4人聯袂出場,聲勢逼人。然后是大規模的巡演。3月7日,台北小巨蛋,縱貫線第一場演唱會,台下觀眾有“台北市長”郝龍斌,知名制作人王偉忠,以及陳升、張艾嘉、庾澄慶等上百名藝人。接下來的香港、北京、上海等地演唱會,據說已一票難求。
專輯的發行,則成為無數樂迷2009年最翹首以待的盛事。低迷的華語樂壇,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的刺激了。
對于羅大佑來說,他要証明,自己并沒有在光榮歷史里沉寂下去,在華語樂壇漸趨平淡的時候,他再次出發了。聚光燈又對准了他,這位几十年中穩坐“華語音樂教父”寶座的藝朮家,會有怒放的第二春嗎?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被過度詮釋過度開采的名字,但是,我們仍然試圖通過近距離的、無拘束的對話,和仔細的打量,呈現另外一個羅大佑,一個音樂之外的、深處的羅大佑。30年漂泊生涯,每座城市的回憶與感悟,對社會和時代的深度觀察,對金錢政治的不遺余力的批判,對于生命的平常心,這些,或許是人們從未領教過的羅大佑的另一面。
羅大佑的雙重生命
無論是在演唱會上公開剪掉自己的美國護照,積極參加“天下圍攻”倒扁運動,還是在汶川地震后出現在加州賑災晚會演唱《亞細亞的孤兒》,羅大佑始終沒有遠離政治運動和社會現實
本刊記者 鄭廷鑫 實習記者 陳小瑾 發自香港
轉折點
1982年,那個叫羅大佑的年輕人,還是醫院放射科的醫生。有一天,他收到了台北市“議員”送來的一袋袋體檢病歷,其中,“有一個人叫謝長廷,有一個人叫陳水扁”。
就在那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在專輯文案中他寫道:“這一趟音樂的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几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走得辛苦的另一個原因,他沒有寫出來,只是在心里掙扎:那時他還沒下定決心選擇做醫生還是做音樂。
父親是醫生,母親是護士,姐姐是藥劑師,哥哥是牛津大學的心臟醫學博士,一家人都以醫學為中心。從在醫學院讀書時組建“洛克斯”樂團,到寫第一首歌,到出第一張唱片,一直到拿了醫師牌照,醫生還是音樂人,這個選擇困擾了他10年之久。
早在他還是實習醫生時,《之乎者也》的錄制就已經開始了。起先沒有人愿意冒險出版這種與市場主流相差極大的音樂。几年后,成立不久的滾石唱片決定推出這張專輯。不料,這個瘦削冷峻的青年一夜之間成為年輕人心目中的叛逆偶像。台灣樂評人馬世芳這般描述當時的情景:“媒體也掀起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在毫無心理准備的前提下,他發現自己已經置身暴風眼的中央,被戴上了‘青年時代的先知兼代言人’這頂大帽子了。”
于是,他一邊當醫生,一邊連續出版了《之乎者也》、《未來的主人翁》、《家》這3張專輯。“回頭看這几張作品掀起的社會效應,其規模之大、延續之久,整個台灣流行音樂史上除了羅大佑,似乎還沒有任何人制造過。”馬世芳如是評價。
但對當時在醫生和歌手兩種角色間游移不定的羅大佑來說,這卻是痛苦的煎熬,“兩邊走的時候,一度覺得自己對兩方面都失去信心。”
1987年,他終于下定決心,給父母寫了一封信,“感謝他們對我作為一個醫生的栽培”,但是,他選擇不做醫生,專心做音樂,“那么多醫生里,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但在音樂上,還有很多發展空間”。
這個決定,讓羅大佑開創了新格局。不久他在香港組建自己的錄音制作公司“音樂工廠”,從事音樂的開發及電影配樂工作。他將對東方曲調的探索,對一個民族的宿命所進行的精確剖析,對黃色人種的濃烈情感和故鄉情懷,以音樂鋪陳開來。
隨后的几年里,他出版了《皇后大道東》、《原鄉》、《首都》。有人說,這是“羅大佑的中國三部曲”,他對香港前途的追問、對台灣根源的探索,對內地變動的思考,躍然于歌中。“一個鋪陳民族命運的史詩企圖,在三張原本各處一隅的專輯之間巍然聳立起來”。
另一個華語樂壇大佬級人物李宗盛談到羅大佑時說:“我覺得從羅大佑之后,就沒有看到有人再做同樣的事。”而在羅大佑之前,同樣沒有人做過那樣的事。“華語音樂的教父”,這個稱呼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于此。
挑戰者
從一開始,羅大佑就以一個挑戰者、叛逆者、孤臣孽子的姿態出現。一身黑衣,長長的黑色卷發蓋住了臉,不苟言笑,永遠戴著墨鏡,這是他最早的形象。
當時的台灣,正處于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威權時代,“胸襟狹窄的執行者,就像坐在角落一邊摔玩具發脾氣一邊啼哭的小孩子”,“醬缸里傳來一股文陰陰的濃重酸氣”。對于羅大佑來說,這樣的環境卻使得那種“多年不見的使命感就這樣無情地冒了上來”。
從《之乎者也》文案里寫的“歌曲審查之,通不通過乎,歌曲通過者,翻版盜印也”,到《現象七十二變》里聲嘶力竭地唱的,“有人在黑夜之中槍殺歌手”﹔從挑釁國民黨的專制到抗議民進黨的腐敗,一以貫之的是他鮮明的政治立場。
1985年,台灣音樂人在“台灣光復40周年”的號召下共襄盛舉,羅大佑創作的《明天會更好》迅速成為廣為傳唱的金曲。年底的大選,國民黨的標語就是“要一個更好的明天”。這首歌成為競選的工具,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政治利用”的責難卻鋪天蓋地般落到他的頭上,這是他日后離開台灣去紐約生活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后,無論是在演唱會上公開剪掉自己的美國護照,積極參加“天下圍攻”倒扁運動,還是在汶川地震后出現在加州賑災晚會演唱《亞細亞的孤兒》,年歲漸長的羅大佑,始終沒有遠離政治運動和社會現實。
“誰要利用21世紀全世界最唾棄的恐怖分子心理來影響選情、制造社會恐慌,誰就是罪魁禍首。”2004年3月27日,為抗議選舉不公正,“泛藍”支持者連續多日在台灣“總統府”前集會,几百名藝人加入其中,羅大佑主動要求講話,發出了這樣的吶喊。
“大佑給我的感覺是他為兩岸三地唱的作品題材比較廣,他會看台灣、香港和大陸的特點、關系,而不僅僅是市場。他很關注香港的政治、經濟,台灣和香港的互動,他是個有強烈歷史感的音樂藝朮家、創作歌手。他這樣定位自己。一直以來,他對自己的作品都非常重視,而且是從一個歷史角度來看待。”羅大佑好友、香港文化人馬家輝這樣評價。
倒扁運動第4天晚上,身穿紅衫的羅大佑來到現場的舞台上,以《心事誰人知》開場,炒熱現場氣氛。接下來他又連續演唱了《戀曲1990》、《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對台下熱淚盈眶的施明德說,“不要掉眼淚嘛施明德,男兒有淚不輕彈。”他帶領著台下的無數人齊喊:“陳水扁,下台!”雙手高舉,聲嘶力竭,激憤滿懷。
馬家輝還提到,“在倒扁高潮的時候,有一個晚上我們在他家喝酒、唱歌,在場的還有一兩個台灣來的作家,唱到最后一句,他把原來寫愛情的詞改成了‘陳水扁下台’。陳水扁敗選、被收押等這些關鍵時間,就算人在外地,他都會打電話回來,報喜一樣。如果在香港,他會約朋友出去慶祝一下。”
2007年,他出席《天下》雜志創刊紀念日的演唱會,獨自在台上清唱了未發表的新歌《吟》:“溶解的恩怨共邀我,別讓你的光輝沉寂。”
采訪當天,我們來到羅大佑家中時,他正在看《信報》,這是一份以嚴肅性在香港娛樂八卦的媒體氣氛中獨樹一幟的財經報紙。交談中,他對內地社會現實的了解超乎我們的想象,他家里的書架插著各種類別的書籍:音樂、政治、歷史、文化……獎杯則隨意地放在角落里。30年過去,他一直沒有稍減對社會的關注和對變動的闡釋,一直在路上。
另一個羅大佑
在歌迷印象中,有兩個羅大佑。一個是搖滾的、哲學的、理性的,用或直白或憤怒或平實的話語來諷刺政治和社會現象、表達個人思考﹔另一個則是傷感的、脆弱的、柔情的,用獨有的長句唱著各種風花雪月的詩和百轉千折的感情。
遠遠望去,羅大佑似乎是犀利的、不好接近的。事實并非如此。對于媒體稱其“孤獨的國王”、“華語樂壇里宛如‘伏地魔’三個字的名字”,他回應說:“什么時候變孤獨?這么孤獨嗎?通常這種人都死掉,而且埋在墳墓里面了。”現在他已經不戴墨鏡了。
“他很講義氣,很關心別人。有時候打電話,我講了一兩句工作上有些煩惱,或者說人際關系上有些煩惱,他不僅在電話里聽我講完,而且過兩天就會打電話來問:你那件事情怎么樣?”馬家輝說,“台灣男人通常不太懂怎樣跟人交往,像他這樣的歌手,去哪里登台,車停在外面,就會有几百人圍著敲車窗要簽名。几十年來都是這種經歷,難免就會過度保護自己。他卻那么體貼,讓我感覺很意外。”
和其他藝人一樣,羅大佑的時間屬于自己的并不多,但他很會主動合理地安排時間。“有時他打電話叫我去聚會,一打來就說,‘家輝我剛到香港,現在在機場往市區方向移動。你等一下,我一個鐘頭就到,我們就在家里聚會。’”馬家輝說,“每次聚會,找誰不找誰,吃什么,他的主意都很明確。有的朋友會說隨便、無所謂,但他總會明確提出想法來。他對生活很有主見、很有要求,住的房子要挂什么畫、要選一些特別的家具,他都會自己去做,很有效率。其他人就算有這個時間,也不一定有這種品位和閑情。他對生活,第一個是懂,第二個是有主見。”
有一次,馬家輝和羅大佑一起參加一本新書的新聞發布會。活動在一個商場舉行,舞台后面有個小房間。“一進去就看到羅大佑在打太極。”這讓馬家輝很意外,“我當時的感覺,這是我見過的最健康的搖滾樂手。”
年輕的時候不是這樣的。在紐約生活,羅大佑整天泡在Disco,“覺得Disco里面才有生命的意義”。隨著年紀的增長,“整個人的眼界開了”,生活方式悄然改變。這兩年他培養起了運動的習慣,主要是爬山,還有就是跟內地一個師傅學太極,這能幫助他“放松精神,緩解壓力”。
與此同時,他依然執著于創作,時刻要求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在我的手臂上有几個自我警惕的煙疤,那是告訴自己勿再胡亂投入于‘思情深似海’的假象。”這可能就是那個冷峻的羅大佑對自己殘酷的一面。
自1996年發行專輯《戀曲2000》之后,一直到2002年,他才開始在內地舉行一系列演唱會。發行新專輯《美麗島》后,他又是久不露面。就在人們覺得羅大佑漸漸沉寂下去,那個年代也漸行漸遠的時候,他又扔出一顆重磅炸彈──與李宗盛、周華健、 張震岳組成“縱貫線”樂隊,繼續另一種形式的創作。
他并沒有真正沉寂,一直都在思考他的音樂,只是“思考的東西越多,感情就越深沉”。“其實我在家里不做什么,就是想事情,這個可能就是我寫曲的狀態。我的活動都在腦子里,我常常失眠也是因為這個,我們的辦公室就在大腦里。”
在酒店里,正在接受媒體訪問的劉德華發現了羅大佑,跑來跟他握手,連稱“羅老師”。寒暄罷,羅大佑高舉雙手,為對方也為自己打氣:“加油加油!”
對話羅大佑
 羅大佑和邰肇玫等
羅大佑和邰肇玫等
 羅大佑
羅大佑
 2004年11月3日,“康熙來了”專訪羅大佑
2004年11月3日,“康熙來了”專訪羅大佑
 2009年2月7日,羅大佑在香港灣仔 圖本刊記者 大食
2009年2月7日,羅大佑在香港灣仔 圖本刊記者 大食 破壞成這樣,我們要趕快修復
──對話羅大佑
本刊記者 鄭廷鑫 發自香港
和羅大佑的訪談,分兩個下午進行,地點從酒店會所到他的家里,話題也不斷地跳躍和發散,總是從預設的題目,自然而然地延伸到社會、時事、歷史和科技。手勢不斷,表情丰富,時而激動時而低沉,時而興奮時而嘆息,這位音樂教父展示了他的喜怒哀樂,泄露了他的真性情。
春晚:十八歲不能唱成八十歲
人物周刊:先求証一個問題。2001年,在新浪網和網友訪談的時候,你說“我大概會寫到2008到2010年左右”,按照這個說法,現在時間快到了。
羅大佑:那時候看起來,寫到2010年是差不多了,沒料到金融海嘯會來,這個事情可能讓我再延續一下。我們在弄縱貫線的時候,根本就沒想過這個問題。去年5月10號,樂隊開第一次記者會,那時候我在台北,隔兩天四川就大地震了,這也是沒想到的。
突然之間,很多事情要去handle(應對),很多題材可以寫。去年發生太多事情了,雷曼兄弟的破產變成一個全世界的問題,聽說全世界的財產從60兆美金跌了一半,這個財產是把股市、樓市、GDP和所有儲蓄都算進去的。你看前几天的新聞,賭王的身家就縮水了9成。
人類的共識從來沒有達到一致,但這次,所有的人類,從歐洲到美洲到亞洲,大家都認同這個經濟危機是前所未有的,這樣的話可能大家會團結一點。
人物周刊:蕭條時期通常也蘊藏著很多機會,你們縱貫線現在有沒有相關的題材?
羅大佑:我覺得《亡命之徒》里,多多少少有點這個影子。那首歌是阿岳(張震岳)的想法,他是從電影里去找感覺,從一個殺人犯要和自己的女朋友分別的角度去寫。討論的時候,李宗盛覺得可以發展下去,我就說,每個人都可以是亡命之徒啊,每個人一輩子總有個時間是像亡命之徒一樣地生活。取得這樣的共識后,我們覺得可以從每個人的角度去找一個亡命之徒。
人物周刊:看了春晚你們的演出,《亡命之徒》只剩下最后一段,還改名為《出發》。
羅大佑:對對對,歌詞改得比較健康一點。
人物周刊:這背后是怎樣一個過程?
羅大佑:也沒什么,上春晚嘛,就是一個預告。從4月18日的北京開始,接下來會有一系列的演唱會,這個時候做做宣傳也不錯。春晚你是知道的,是給沒有新意的人看的,所以我們也按照上級的指示,哪里不能做就不做。阿岳有一首《愛的初體驗》,講到“是不是我的十八歲”,現場把歌詞打出來,我說我們唱成八十歲好不好,那邊就說不行,一定要唱十八歲,歌詞怎么打就得怎么唱,一板一眼,完全不能有失控的感覺。這蠻有趣的。
我贊成兩岸慢慢地、自然地走到一起
人物周刊:現在回過頭,怎么看台北?
羅大佑:我現在反而最不會形容台北了,一個人一輩子最不會形容的大概就是自己的家鄉,自己出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現在把台北當作自己的家了?
羅大佑:還是有點猶豫。不過現在好多了,自從去年5月,馬英九上台之后,就好很多了。陳水扁嚇死人了,前所未有的嚇死人。
人物周刊:他們一家這几個月占據了很多報紙的版面。
羅大佑:你看這個人,在總統府里搞成這樣,在監獄里還能搞成這樣。(邊搖頭邊笑)
人物周刊:你現在還是在關注那邊的新聞吧?
羅大佑:重要的新聞都會關注。比如說台灣的經濟,很多人都說,哎呀,馬英九沒什么希望,做不了太好。我覺得陳水扁搞了那么大一個爛攤子,其實李登輝的后期已經很糟糕了。馬英九一上來就碰到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藍綠的對立還是很緊張,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給他多一點時間。奧巴馬當選之后的演講說了,金融海嘯可能不只一年,甚至不只在總統的一個任期之內就能結束。你想要馬英九怎么樣嘛。
人物周刊:很多人覺得馬英九上台,會讓兩岸關系往好的方向走,你怎么觀察?
羅大佑:我覺得兩岸應該往自然的方向走,不要硬是把關系搞得太僵了。我比較贊成兩岸慢慢地、自然地走到一起來,不要太牽強地統一,就像香港和大陸,你要太快也是不可能,麻煩事會一大堆,兩邊本來就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又說到金融危機可能是個好事情:當人類發現每個人都那么危險的時候,惟一的辦法就是大家要彼此信任,每個人都要更努力。人是我們惟一可以相信的共同體,難道你要相信空氣嗎?相信海水嗎?相信動物嗎?我覺得每個人在危機里都只能夠相信其他人,所以會更團結。
我是樂觀的。現在大家經濟都不好,都需要共同度過這個難關,政府和銀行系統的前所未有的合作也是希望把這個難關解決掉,這些都是空前未有的。溫家寶這次去歐洲,應該就是談論金融這方面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對時事的關注挺多的。
羅大佑:這個很重要嘛,亞洲、歐洲、美洲現在是鼎立的,就像中國小說里講的三國時代,亞洲現在變成了美洲跟歐洲之間的協調者,大國崛起就是這樣,我覺得現在怎么去扮演一個好的協調者,去幫助另外兩個洲,這是好的事情。中國這個名字,本來就有一個“中”嘛,有點中庸的、中間人的味道。
人物周刊:可是,中國人也經常相互埋怨對方,要么太左要么太右,就是不夠中。
羅大佑:你要反過來想,你批評我太左或者太右,其實你是想中的,才會注意到我是不是太左或者太右。中國人是想中而不得其門而入啊。其實中國人是一個蠻矛盾的民族。我覺得歸于自然是比較符合中國人的哲學觀,像老庄哲學就是,從中國的音樂里可以聽出來,從國畫里也可以看出來。
為什么要打倒崔健?
人物周刊:當時你離開台灣去紐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羅大佑:從《明天會更好》那首歌就開始了,那首歌基本上就是被政治操作出來的。當時,黨外的人批評我被國民黨利用,批評我變節跑過去幫國民黨﹔國民黨的人又覺得,我寫出這樣的歌不倫不類。兩邊都不是人。
人物周刊:那時有一個逃避的心理?
羅大佑:當然有,我覺得在台灣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容下我,完全被排斥在這個社會之外,這樣很辛苦的。
人物周刊:到了紐約,可能意味著從零開始。
羅大佑:對對對,歸零就對了。英語有一句話是“When you are nothing to lose,you win”,你什么都沒得可輸的話,你就贏了。如果還在意我是羅大佑、在意那么多掌聲的話,你就會損失很多。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活得理直氣壯了嘛。
人物周刊:你在紐約的生活怎么樣?
羅大佑:我跑到最亂的、一般來講中國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為什么?
羅大佑:我覺得這樣才踏實,敢在台上唱歌的人,就應該敢到那么危險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站在台上很危險嗎?
羅大佑:很多人忽略了,其實舞台蠻危險的。我說的舞台不是一般人講的舞台,而是一個focus。比如在媒體上,你是所有人注意到的focus,你講的話可能會被人斷章取義,那是很危險的。像狗仔隊那樣的拍照,你交個女朋友、去夜店之類,都要偷偷摸摸。公眾人物都會面對同樣的問題,都是危險的。
搭得不好的話,演出的舞台也是危險的。華健就碰到過,舞台搭得不好,從上面掉下去,全身都是血。
人物周刊:現在回頭看紐約,那是一個什么樣的城市?
羅大佑:紐約肯定是全世界最深的一個都市,最大的一個人類原始叢林,它有全人類最好的和最壞的東西,最大的罪惡和最好的人性都在里面。
人物周刊:在紐約的時候都做些什么?
羅大佑:我那時候去考醫生執照。臨床醫學考過了,基礎醫學還沒考。基礎醫學要念很多書,藥理、解剖,一大堆。那時候本來想放棄音樂的,后來跟各種人接觸多了,覺得搞藝朮還是很好,比較踏實,是我自己喜歡的。
人物周刊:那邊的藝朮家是怎樣的生活狀態?
羅大佑:他們會自己做木工活,比如我說我的窗戶壞了,幫我修一下,他們就帶著整套工具過來,很專業的樣子。紐約的那種氛圍很好,藝朮家之間會互相支持。你要開一個party,我一定會到。中國沒有那樣的氛圍。
華人世界的藝朮家,相互的支持不夠。你看中國人要搞一個band (樂隊),特別難。像我們縱貫線,都是有十几二十年音樂經驗的人,知道團結很重要,我們知道,阿岳可以打鼓,大佑會彈keyboard(鍵盤),李宗盛在弄那個木吉他,華健雖然電吉他彈得不好可是很喜歡這個工作,所以樂隊很快就能上手。
最重要的是幫助對方把這個空間開拓出來,支持你就是支持我自己。大家都需要這個天空,這個天空是我們共同的天空,當我們把這個天空創造出來后,它就是人民的天空,是所有人的。
我覺得華人世界有一點比較奇怪,好像崔健做到No.1,我就要打倒崔健。這個概念是有問題的。你為什么要打倒崔健呢?你走另外一條路不就得了?很奇怪。羅大佑走了這條路,你就不能走一條非羅大佑的路嗎?你干嘛要做另外一個羅大佑呢?為什么要做另外一個羅大佑來打倒羅大佑呢?不值得嘛。
在香港,太大膽你就沒朋友了
人物周刊:從紐約來到香港,從西方回到東方,會不會有不適應?
羅大佑:還好啦,都是資本主義,在這個社會上誰也不管誰。不過,畢竟還是中國人的地方,創作上你大膽一點,就會有朋友說,小心點,不要拖我們下水啊,別累到街坊了。如果你太大膽,就沒朋友了。在紐約,創作上是誰也不管誰。
人物周刊:當時為什么要來香港?
羅大佑:1986年,我從紐約來香港,擔任一個音樂比賽的嘉賓。我發現香港正在面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事情叫“七一”,我覺得這是人類歷史上很大的一個事情,一個人一輩子可能都不會碰到一次。那段時間,我在香港寫了《東方之珠》,連詞帶曲,沒記錯的話,是1986年的9月到11月。
那時候想想,我還是決定做音樂。1987年4月,我給父母寫了一封11頁的信,當時他們很擔心我做音樂,我說我還是喜歡做音樂,你們要相信我,不會讓你們失望的。寫了那封信之后,他們就不再擔心我了。
紐約讓我認識到artist(藝朮家)的正常狀態。香港讓我認識到比較好的創作制度,香港有作詞作曲人協會,各種制度,包括版稅制度比較完善,創作的自由也比較有保障。
那時候香港的翻譯歌還比較多,翻譯了很多日本歌。我做的是中文原創歌,我總覺得中國人還是要創作中國人的歌曲。
人物周刊:如果不做音樂,你現在會是一個好醫生嗎?
羅大佑:不敢講是好醫生,但也是不壞的。我是那種集中精神之后就很難分神的人,但集中精神之后,我會給自己很大的壓力。醫生這個行業其實不是太快樂的,很嚴肅,我做音樂已經這么嚴肅了,再去做醫生,肯定會給自己更大的壓力。
人物周刊:那時學到的東西,現在還有用嗎?
羅大佑:有用有用,我想整個醫生的行業,都是在學習怎樣面對生命、尊重生命。音樂也是這樣。創作都要講感情,感情是生命里最重要的東西。
醫生看的生死比較多,可能會無情一點。醫生是必須借著無情來表達他的有情,創作則是借著有情來表達生命的無情。
人物周刊:當時對于自己做音樂,有沒有懷疑過?
羅大佑:當然有,我到現在還在懷疑,擔心自己隨時有可能下一首歌寫不出來,一直都有這個擔心。這個擔心是對的,會讓我把創作出來的每一首歌都當成是上天的恩賜。
北京松綁了,中國就松綁了
人物周刊:后來,你在內地也生活過。
羅大佑:在北京和上海都住了一年多。北京是2002年3月初到SARS之后。最奇妙的是廣州的演唱會,我是2月18日在廣州開演唱會,正好過几天是中國國家隊打巴西,也在天河體育場。那是SARS最厲害的時候,那天又是我爸爸過世5周年紀念日,這對我特別重要。演唱會之前,我在北京問了很多朋友,你們有沒有聽到消息,我從香港帶了一些口罩,你們拿去用吧。
人物周刊:為什么會去北京生活呢?
羅大佑:去北京之前在台北。2000年,陳水扁上台后,我覺得台灣怪怪的,覺得李登輝出賣了連戰讓陳水扁贏了。台灣看起來很民主,但這種民主后面有一種很大的欺騙成分,有很多操作在里面。
我覺得藍綠的斗爭,根本就是民進黨搞出來的,后來也証明了,這是一場像“文革”那樣的,左派跟右派之間的斗爭。這個人不是左的就是右的,沒有中間路線,“反右”就是這樣開始的。民進黨把自己定義成綠色,像我這種無黨無派的人,就把我弄成藍的。我什么時候支持過國民黨啊?我的歌都是在國民黨時期被禁的,但就是被打成藍色了。我感覺在台灣已經住不下去,就想去北京試試,找個四合院生活一下。
人物周刊: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樣?
羅大佑:北京的生活還是不錯的,但我覺得北京的官僚氣氛太重了。北京好像每個人都有個親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樣。現在回頭看看,也蠻有趣的,這段時間是北京變化最大的時候,就這五六年,肯定是北京歷史上變化最大的時期,不只是因為奧運。像建筑,這几年新建了好多,整個都市的樣貌都變了。
人物周刊:你覺得這是好事嗎?
羅大佑:有好有壞。為了跟世界接軌,這樣是好的﹔為了把中國傳統的官僚氣瓦解掉,這也是好事﹔還有甩掉歷史的包袱。中國背著很重的歷史包袱,而北京的包袱肯定是最大的,北京要是不把這個包袱松綁的話,中國就很難輕松了。北京松綁了,也是中國的松綁。壞處是,我們和中國文化之間,會不會造成一個脫節,掉到科技的漩渦里。
人物周刊:文化的脫節會造成什么后果?
羅大佑: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不會寫中國字是很嚴重的,比西方人不會寫ABC更嚴重。西方人只要認識26個字母,但中國字很多,象形文字嘛。你要是連象形文字都不會寫,這個文化就很危險,就沒有認同感了。我一直覺得認同感很重要的。日本的沒落我相信跟這個國家的脫亞入歐有關系。日本到1980年代的時候,經濟全世界第一,可是你看現在就不行了。雖然日本這個國家很干淨,日本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可是你會覺得這個國家缺少了一個東西,少了一個根本,所以亞洲人都不喜歡日本,歐洲人也很奇怪,你日本人怎么會覺得自己是歐洲人呢?成了四不像了。所以說,人一定不能忘本。
人物周刊:你覺得對你這一代台灣人來說,你們的本是什么?
羅大佑:我覺得不管台灣人怎么樣了,跟中國必定還是有關系的。就算是原住民,跟中國人在血緣上、地域上都是有關系的。你不能硬把它切開。在台灣做那些去中國化的事情,是很愚蠢的,你還是用筷子吃飯的嘛,除非你硬要訓練所有人都用刀叉吃飯,但是這可能嗎?
我覺得認同,不管是怎樣的感覺,都是一種普世價值。人畢竟是情感的動物。我想我們認同的都是一種不具有大的破壞性的價值,一種有安全感的自由的價值,就像羅斯福講的,人有免于恐懼的自由,這是人的權利。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羅大佑:1985年非洲飢荒的時候,要求支援非洲的,全部都是藝朮家。你看藝朮,講的都是人心里面追求的love,人類的愛、和平共處,所以他們最反對的就是破壞者。破壞者就是戰爭、飢荒、疾病、政治迫害等等。
羅大佑:只要我的歌能流傳不用記得我是誰
琢磨上海,研究廣州
人物周刊:后來你又去了上海,你覺得上海怎么樣?
羅大佑:我覺得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4個城市里,最相同的兩個是上海跟香港,所以會有一個銀行叫香港上海匯丰銀行嘛。(大笑)這兩個城市太像了,匯聚了很多丰富的東西。大家都不啰嗦,追求利益,精打細算,然后,追求最update的一些東西,從fashion,到news,到information,到股市什么的,CNN最近播什么,YouTube里面最新流行的視頻。大家都知道金錢的價值很重要,這是很現實的,金錢不是第一的,但永遠都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不斷地換地方生活,是為了體驗,還是為了尋找一個對你來說比較有安定感的地方?
羅大佑:可能也是一種好奇心吧。1997之后,內地在很多方面幫到香港,同時香港也帶給內地一些新的東西。短短10年之間,那種全球化的速度,讓人感覺中國并沒有在世界之外。這十几年里中國的變化,比從1997追溯到1901年的變化都大,從這里就可以看出,香港這個窗口是多么厲害。
還有廣州,廣州以前是扮演香港現在的地位。我去每個地方做演唱會之前,都會做一些study。我發現,廣州有全中國第一個做槍炮的實驗室,近代以來,很多最先進、最革命性的東西都是從這里開始。所以說,廣州的開放要比上海悠久,上海開埠大概就兩百年時間,廣州大概600年前就開始了。我發現一些英文詞匯的引進,是從粵語開始的,像我們把英語的John叫做約翰,用廣州話來讀,就很接近英語的發音,用國語的發音不像的。用國語將Peter讀成彼得,Paul讀成保羅,Mary讀成瑪麗,都是這樣的。
新世紀來勢洶洶
人物周刊: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你經常提到新世紀,現在新世紀第一個10年已經快過去了,覺得新世紀有什么不同?
羅大佑:新世紀來勢洶洶,來勢洶洶啊。我覺得新世紀最不同的,是科技的泛濫。從1990年代,開始感覺到電腦的厲害,到21世紀,電腦更厲害,IT的普遍性更可怕,網絡的普遍性更可怕,從google一直到YouTube再到facebook,越來越多,很多東西變得越來越空。
我覺得現在人類好像已經到了這樣一種情況,就是共識會越來越多。所有的媒介和科技都在改變人的觀感。以前查一個資料,要辛辛苦苦打很多電話,上圖書館才能查到,現在上網一輸入關鍵詞,嘩啦啦都是信息,到了你看不完的地步。這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是所有人的問題,我們都面臨一個太多的問題,而不是太少的問題,這很可怕。這是第一個共識。
第二個共識,每個人都覺得錢不夠,但是又沒有大問題出現。雖然金融危機來勢洶洶,但媒體和科技的發達,快速有效地警告了所有人,大家也很有准備地慢慢調到相應的水准,不會像以前一樣,一下子就跳樓的,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得亂七八糟的。
現在看起來,姓“社”的想姓“資”,姓“資”的想姓“社”,美國現在就是特別想姓“社”的感覺嘛。這好像跟當初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特別吻合,很和諧嘛。所以說,現在在香港待得挺好的,香港不就是一個姓“資”又姓“社”的地方嘛,所以我們在這里都很幸福,很合乎世界潮流。(大笑)
人物周刊:你好像對科技的東西比較警惕。
羅大佑:我很小心科技,因為我做過香港第一個48軌錄音室,我知道科技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比如說速度越快的車,產生的車禍就越可怕。越是高科技的東西,出問題的時候,越嚴重。這種東西一定要小心。音樂方面,MIDI太強大了,很可怕。還是得回到人自身。
人物周刊:你有點反現代化嗎?
羅大佑:我不是反現代化,我覺得現代化的東西要接觸,知道什么是現代化之后,就要回來,去尋找人跟科技之間的平衡。人跟科技跟大自然跟這個世界,要永遠處在一種平衡的狀態里。
現在我想有個孩子
人物周刊:你是客家人,這樣四處跑,跟你的客家人身份好像比較相符。
羅大佑:血緣大概是有點關系的,我父親也是一樣,從台北跑到苗栗又跑到高雄。
人物周刊:你的《昨日遺書》里有這樣一句話,“小時候,全家人都不善于向彼此表達感情”,這對你有影響嗎?
羅大佑:可能有影響。在現實生活中不太會表達,就要放到音樂里來表達。
人物周刊:你父親的去世對你打擊很大?
羅大佑:很大,非常大。不過另外一方面講,我父親去世后,我就變得越來越自己了,重新開始扮演自己。
人物周刊:你在《鏘鏘三人行》里說的第二人生,就是這個概念?
羅大佑:對對對,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人物周刊:第二人生是怎樣的概念?
羅大佑:一般人來講,從父母生你,到走進社會,到有了自己的家庭,第二人生就是有了小孩以后。但是我沒有小孩子,我現在是想生個小孩子,以前覺得會束縛自己,可能是現在年紀大了。自從父親過世以后,覺得好像是他的生命延續到我的生命里,我也想把我的生命再循環下去。
人物周刊 :《昨日遺書》里也說到母親,“上學第一天在教室從頭哭到尾,因為媽媽不見了”,“更想回到她的體內”,這算是一種戀母情結吧?
羅大佑:這個東西每個人身上都有的。你從生下來,一直到上學,都是媽媽在照顧,突然到了一個群居的地方叫學校,旁邊都是你沒看過的人,有個新的人叫老師,這個角色一時還沒辦法接受,哭了好几天。
人物周刊:后來你母親中風了。
羅大佑:是的,在紐約中風。腦血管里有一個動脈瘤,破掉了。她有高血壓,特別容易破掉。我哥我姐我姐夫都是醫生,破掉之后他們還不知道,沒留意到是中風,因為她還有青光眼,以為是這個問題,都反對開刀,就我一個人贊成,因為在紐約這樣的大城市,開刀是沒問題的,最好的醫生都在這里。到了醫院,醫生說,怎么現在才來開刀,說的話跟我一模一樣。我的專業知識終于用上一次。(笑)
人物周刊:20年前你選擇了做音樂不做醫生,現在覺得這個選擇有什么得失?
羅大佑:當然有得有失。失去的可能是一份很穩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到現在都過得不錯,這是相反的一種生活,一種比較漂泊的日子。過去這10年,我至少搬過10次家,搬家對我來說是很平常的事。
中世紀有一種吟游詩人,到處唱歌,到處跑一跑看一看,到一個小鎮住一段時間,寫一些歌,看一些不一樣的人、不一樣的風土人情。我到現在多多少少還保留著一點吟游詩人的感覺。在21世紀還能過這種生活,我覺得蠻難得、蠻奢侈的。缺錢的時候就出來唱一唱,賺一點錢,寫一些歌,做一點電影配樂。政治人物像陳水扁那樣的,看著不爽就罵一罵,好像也不錯的。
人物周刊:你在自己的音樂和書里,一直說到“家”,它既是你要逃離的地方,又是你要回歸的方向。現在,你想得更多的是逃離還是回歸?
羅大佑:現在是想回歸比較多,到了一定年紀了。我是巨蟹座的,巨蟹是比較內向的,總喜歡在家里東弄西弄,把家布置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人物周刊:現在的狀態還不錯吧?
羅大佑:還OK啦,我覺得生活只要保持一種OK的狀態就行。可能也跟沒有小孩子有關系,有小孩狀態就不一樣。我后來發現,有小孩的家庭和沒小孩的家庭,差別是蠻多的,因為你的生活重點會不一樣。我要搬家的話,隨時都可以走,沒什么顧慮。很多父母要搬家的時候,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小孩的教育環境問題。
人物周刊:那你還是想要小孩?
羅大佑:我有點想耶,我也想改變一下生活嘛。
人物周刊:想過再成立一個家嗎?
羅大佑:這里就是我的家嘛,自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但我隨時都會搬出去。至于要去哪里,跟整個中國的變化有關系。我還是想到處看看,發生了什么。中國現在變得蠻厲害的,這種改變比起20年前的那種改變,差別是很大的。
只要我的歌能流傳,不用記得我是誰
人物周刊:做樂隊這個想法怎么來的?
羅大佑:最早的想法從前年、大前年就開始,一直在想要起什么名字,哪些人來合作,其實也跑不了這几個人。
人物周刊:縱貫線成立的原因,有兩個非官方說法:一個是“救市說”,為滾石的唱片市場救市﹔一個是“救命說”,要感動陳淑樺走出自閉。
羅大佑:淑樺現在是在比較封閉的狀態里,我們想能不能給朋友一些幫助,做一些事情。4個男人加一個女的,我們可以寫一些歌,我想等到我們4個弄得比較成熟一點再找她可能會好一點。
人物周刊:縱貫線成立的時候,你們說,“要搞非常之建設,先搞非常之破壞。”這個破壞怎么理解?
羅大佑:當初寫這個有點聳動了,有點故意要引起注意才寫的。現在不必去搞破壞了,整個環境已經被破壞成這個樣子了,我們要趕快去修復一些東西。(笑)假如在2009年,有一首像《明天會更好》那樣,可以激發大家士氣的歌曲出來,也不錯啊。雖然我很不喜歡《明天會更好》這首歌,但假如有一首不同風格、能起到同樣作用的歌,我覺得是很好的事情。
人物周刊:之前有個說法,說這個樂隊成立1年就要解散。如果市場反應特別好,有沒有可能繼續做下去?
羅大佑:1年應該是差不多的,我覺得不要再延續下去。可以用其他的形式,各自做自己的,因為我還有音樂劇要做,我現在一直在寫音樂劇。
人物周刊:寫什么樣的音樂劇?
羅大佑:跟下一代會有關系,跟兒童會有關系。
人物周刊:另一個《未來的主人翁》?
羅大佑:類似于這樣的,但是比較喜劇式的,跟這一代、下一代之間的那種錯綜復雜的愛情啊、婚姻啊、教育啊都有關系。
人物周刊:有沒有想過做完音樂劇之后,或者說到了某一天不做音樂了,你會做些什么?
羅大佑:我想音樂還是我終生的職業,因為跟音樂有關系的東西太多了。科技的發達使每一種行業都連結在一起,但還是要跟音樂有關系,沒有音樂會覺得怪怪的。我現在就在幫杜琪峰的一個電影《復仇》做配樂,一個法國投資的電影。這些行業都是分不開的。
我覺得在這個時代,這個環境下,你在本行做得好,也可以在其他行業做下去,不用擔心失業的問題,只怕你沒有專業的技能。
人物周刊:你會不會害怕被遺忘?
羅大佑:還好。我一直覺得我是處在被遺忘的邊緣狀態。從《戀曲2000》到《美麗島》,差不多10年時間,不也是半被遺忘的狀態嘛。
人物周刊:很多藝人害怕這種感覺。
羅大佑:我不怕,尤其我是以創作為主的,自己把自己看得比較幕后一點,干擾少一點,比較適合觀察。我是那種死掉之后,只要我的歌還能流傳,不用記得我是誰都沒有關系的。只要歌還在就好。
人物周刊:《昨日遺書》這個書名,好像是要跟過去告別。
羅大佑:人生對我來講,一直都是一個個的階段,你到了一個階段之后,就會覺得是跟上一個階段告別。寫那本書是在1987年剛到香港的時候,那時是在跟離開台北的那個羅大佑告別。當然不可能完全告別過去,只是希望更清楚地活出一個新的未來,在新的環境里做一些新的事情。時代也在改變。從1980年代到1989年,到1997年,到2000年,到美國的“9﹒11”,到SARS,一個演唱會又一個演唱會,一個都市然后又是一個都市,都不一樣。風景在走,人也在往前走。或者空間沒動,可人都過去了,永遠過去。
人物周刊:等到哪一天真的要告別的時候,你希望墓志銘上刻些什么?
羅大佑:我想過這個事情,以音符來表達生命的人的下葬地,大概是這樣。我是用音符來表達我對生命的觀點的,我所有的情感和觀點都在音符里。
羅大佑的局限
歷史紛亂時,羅大佑展示的是大國小民坐看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聰明。大局漸定時,羅大佑展示的是人世無常、浮生若夢、世事滄桑的感悟
李皖
羅大佑到底有多尖銳
羅大佑頭上有反骨。在洪山體育館他對著台下說:你們就不要再搖熒光棒啦,都那把年紀啦,不要裝。
頭上有反骨的人,才會這樣刻薄地說話。那一刻,我在思考這長反骨人的命運。
1982年,《之乎者也》橫空出世,羅大佑被譽為“青年時代的先知兼代言人”,展開新舊價值觀激烈交戰的戰場。
檄文第一篇是《之乎者也》。羅大佑挑戰了什么?他挑戰了──保守政局下的校風整治、校園歌曲的風花雪月。大陸也有過那個年代,古板校風對抗著開放的時尚,卷發、長發、喇叭褲都不准進校園。1982年,羅大佑叫板的就是這。
羅大佑以敢罵著稱。陳水扁當政的時候,他罵過陳水扁﹔他還挖苦過李登輝,戲謔過開放搞活。八九十年代之交,他嘆台灣,憂香港,譏大陸。如此以歌曲形式批遍華人政治,是誰也無法超越的紀錄。
罵陳水扁,說他是“綠色恐怖分子”、“南台灣的水蓮槍擊騙子”,而台灣民眾是在“見証民主自由的無知”(《綠色恐怖分子》)。1994年,大陸、香港、台灣局勢有了轉機的時候,羅大佑嘲諷政治立場讓位于經濟利益,把三地人民在新時期的作為看成拼命賺錢、炒股、賭六合彩的一場笑劇(《五十塊錢》)。
大佑喜歡放大炮,夠狠,但是缺少余韻。論批判眼光,他并不銳利,而是尖銳不足,刻薄有余。
長反骨的人,喜歡放惡聲、開頭炮。有這種個性的人,膽兒大、嗓門大、性急、毛躁。亂世生梟雄,振臂一呼天下動,第一個說出了你想說的話題,但是批評是那么表面,事件一過往往即告失效。
在時代的亂局中,批評家羅大佑,并不是個洞穿了歷史黑幕的人,他同樣蒙在鼓里,偏巧又喜歡置身事外,冷言冷語。在深刻的轉機面前,他屢屢試圖舉起洞穿的長矛,但他看到的是那么少,總是膚淺片面,單一而情緒化。他看不清靶子,只看清了最大個的噱頭,要“敢把皇帝拉下馬”!這不是真正的批判者所為。真正的批判者,從來不會跟傀儡較真,而會看到傀儡下面的歷史力量,看到時代精神、社會思想的盤旋糾結,不說如此批判能管300年,但若干個時期過去,另一個時期的人應依然能印証、體會。
羅大佑到底多有思想
在不同時期,羅大佑曾閃念過不同的思想。
1980年代,他發現了變化,發現了時代的告別。
這一時期羅大佑的思想盤桓在這些方面:變化之年,鄉村與都市、傳統與時風在人的心靈層面的深刻沖突(《鹿港小鎮》)﹔台灣,進而整個亞洲,受制于西方政治力量,飄搖如一葉小舟的命運(《亞細亞的孤兒》)﹔城市眾生相,生活的質量并不隨物質文明的提高而進步多少(《現象七十二變》)﹔對未來的憂慮,所憂慮的包括當下的科學、政治、社會規范勢力對未來一代的塑造和影響(《未來的主人翁》)﹔出走與出走后對家的渴望(《家Ⅰ》、《家Ⅱ》)﹔對城市垃圾、治安、塞車、市政建設的批評(《超級市民》) ﹔愛情、不朽、夢想、真理的不確定及其對它們的懷疑(《我所不能了解的事》)﹔人的本性──上帝、魔鬼共住心中的事實(《耶穌的另一個名字》)。
1990年代,羅大佑發現了動亂,發現了黃種人的共同命運,發現了兩岸三地交錯共織的一場歷史大戲。
他心憂香港的“九七之變”,為它未知的命運祈禱(《東方之珠》等)。他追溯台灣的戰亂頻頻、割地入侵、島民勤耕苦作的斑斑血史,力圖為它找到最終歸屬的根(《原鄉》等)。他笑望大陸的改革開放,描繪出五千年首都大門終于開啟,股票地產旅游特區、走私賭博招商炒樓、精神污染包二奶一時齊飛的熱鬧景致,不管道理,不深究其變,總之一概搞笑之(《首都》、《飛車》、《親親表哥》)。
這時的羅大佑,最逼近歷史巨變的軸心。在華語歌曲中,第一次有人如此清晰而深切地表現出這樣的情緒:“啊,如此的動亂搗向何方/為何,每個人內心難以估量?”(《動亂》)
但思想家羅大佑是如此地膚淺。他有觀察歷史的雄心,卻缺少觀察歷史的方法﹔有洞察世事的渴望,卻沒有與之相匹配的力量。
最能代表早期羅大佑的大作,無論《現象七十二變》還是《未來的主人翁》,今天看來,它的思考是那樣淺,容量是那樣小,詞義淺顯得簡直讓人不堪忍受。而后期羅大佑暴露出另一個命門,他的思想都是斷章,他前一個時期發現的命題,再沒有在后一個時期深入。結果每一個時期,他的思想都成為因時而動的閃念,成為片斷化的小碎片。
以歌曲思想史的角度看,這是一個抱負遠大,卻因為才疏學淺、勢單力薄,而最終未能將自己成就的人。
一口氣以音樂工廠名義推出《皇后大道東》、《原鄉》、《首都》,是羅大佑思想最為雄渾、博大的時期。此時的羅大佑,是華語歌壇上睥睨天下首屈一指的戰略家。但羅大佑并不是個思維清晰的人,到稍遠一點的1994年,思想家羅大佑已經說不出話了:還是面對著這場華人世界的大局,《戀曲2000》卻生長出藤蔓交錯的比喻和象征,思想全無,只剩下幻滅的,不安的,憂心忡忡、患得患失、追悔莫及又恍若隔世的末世情和亂世情。
歷史紛亂時,羅大佑展示的是大國小民坐看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聰明。大局漸定時,羅大佑展示的是人世無常、浮生若夢、世事滄桑的感悟。這依然局限在中國傳統哲學的套路里,勿談超越,僅僅是個一般的學舌者所為。思想家羅大佑的重量,靠的是比當世所有人都更濃烈更沉重的感情。在最極致的1994年,它的慘烈、強大,直比天地之氣。
羅大佑的詞到底有多好
世人欣賞羅大佑,多欣賞羅大佑的詞。
世人欣賞羅大佑的詞,多欣賞羅大佑那么多的形容詞,那么長的曲折復雜、奇妙連綴的長句。
當然,他肯定說中了你的心事。但麗辭靚句只是末技。
作為歌曲,詞與曲是一個整體,單獨地去評論詞,肯定有它的偏頗。羅大佑的詞,為了完美地配合先做成的曲,往往耗費三五年之功方告完成。
但詞是一門單獨的手藝。曲調既成,他開始單獨與詞作戰。就詞而論詞,當能端量出一個人的文字水平。
作詞家羅大佑,水平忽高忽低,時好時壞。
大佑詞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有這么多未完成之作。何謂未完成?語病多、境界普通、思維散亂、修辭水平不高、需要修改的詞叫做未完成。粗略估計,這部分詞將占羅氏全部作品的至少一半。
羅大佑罕有文字上無可挑剔的詞。這樣的詞多集中在早期,多集中在他的詞作小品,其思想大作大都失敗。早期完美的羅大佑詞,格局都比較小,如《戀曲1980》、《童年》、《光陰的故事》、《愛的箴言》,都是一些精美小品。顯示羅大佑襟懷和氣象的作品中,只有那些境界中等的寫到了較高的完成度,如《鹿港小鎮》、《將進酒》、《家Ⅰ》、《家Ⅱ》、《我所不能了解的事》、《耶穌的另一個名字》、《一樣的月光》。
羅大佑中后期詞作境界極高,出現了一個飛躍,但也只是小部分作品寫到了完美。文字上難于挑剔的作品有:《游戲規則》、《動亂》、《上海之夜》、《台北紅玫瑰》、《戀曲2000》、《舞女》。作為一個詞作家,他缺少洗練文字的能力,往往語義糾纏重復,思維比較混沌。
但恰恰是在混沌的思維里,羅大佑創造出了惟他獨有的文字。偉大的詞作,從來不是因為詞句之功,而是文體創新,意境氣韻獨到,情緒、精神或思想卓越,道人所未道。羅大佑文字才能絕非一流,卻進行了以下探索:他創造了抽象的對象含糊的敘事詩,這在歌曲歷史上獨有﹔他創造了虛構的注重戲劇性和氛圍的歷史詩,在華語歌曲里如行在天空的宙斯。前一種詩有《戀曲1990》、《你的樣子》、《滾滾紅塵》、《追夢人》,意境上有纏綿之極的深境、前人所不及的淒美 ﹔后一種詩有《京城夜》、《東風》、《藍》、《天雨》,為了難于解釋的大時代,造出了無法解讀卻令人神魂俱驚的歷史大夢。它們不完美,卻是最了不起的大佑杰作。
在語言上,羅氏還曾經有過一個特色,大量轉借中國革命語匯,以移用、戲仿手法,構成了中期羅大佑詞作的修辭特征。但是除了一點有趣,這一部分羅氏歌詞在意義上卻比較空洞。
波瀾壯闊的歷史大幕的開啟者,有絕世的影響力,但也同時并存著膚淺的思想與批判,這是開啟者的歷史局限。而作為音樂家,主要是用情感說話,即使思想卓越,也只能略過,這是音樂家的宿命。而作為歌曲作者,創造出優秀的歌曲最頂真,文字爛點兒也在所不惜。對羅大佑的局限,當如是觀。
羅大佑年表
1954生于台北
1974發表第一首創作歌曲《歌》 (電 影《閃亮的日子》插曲),同時期創作《鄉愁四韻》
1982發行首張個人專輯《之乎者也》,并在國父紀念館舉辦演唱會
1983推出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
1984發行第三張個人專輯《家》,
12月31日在中華體育館舉行“最后一個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告別演唱會,暫別流行歌壇
1985赴美
1987在紐約獲頒“亞洲最杰出藝人獎”,同年定居香港
1988推出專輯《愛人同志》
1990在香港成立“音樂工廠”
1991粵語專輯《皇后大道東》在香港發行,囊括香港三大排行榜冠軍。同年推出以台語歌曲為主的專輯《原鄉》
1992推出粵語專輯《首都》
20009-10月在上海、杭州、南昌、昆明舉辦“世紀巡回演唱會”
20019-12月在深圳、西安、南京舉辦巡回演唱會
20043月27日參加“要真相、拼公道、搶救台灣民主”抗議活動,高呼“不分藍綠,只要黑白”,隨后在台北、高雄、台南、新竹、台中展開“羅大佑台灣巡回演唱會”
200411月推出專輯《美麗島》
20058月26日,羅大佑“之乎者也”演唱會在北京舉行
2008 與李宗盛、周華鍵、張震岳成立縱貫線樂隊
獲獎
1987 亞洲最杰出藝人獎
1987 金嗓獎最佳作曲獎(《意亂情迷》)
1990 第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配樂獎(《衣錦還鄉》)
1990 金馬獎最佳電影主題曲獎(《滄海一聲笑》)
1991 第1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主題曲獎(《滄海一聲笑》)
1992 金曲獎最佳單曲歌唱錄影帶影片獎(《火車》)
1992 金曲獎年度最佳單曲獎(《火車》)
1992 第1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主題曲獎(《似是故人來》)
1993 金鼎獎最佳作詞獎(《大地的孩子》)
1993 新加坡第1屆醉心金曲獎10年風云人物榮譽大獎
1993 第3屆《中時晚報》唱片評鑑大獎最佳制作人獎
1993 第3屆《中時晚報》唱片評鑑大獎最佳專輯獎
1994 第1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主題曲獎(《女人心》)
南方人物周刊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