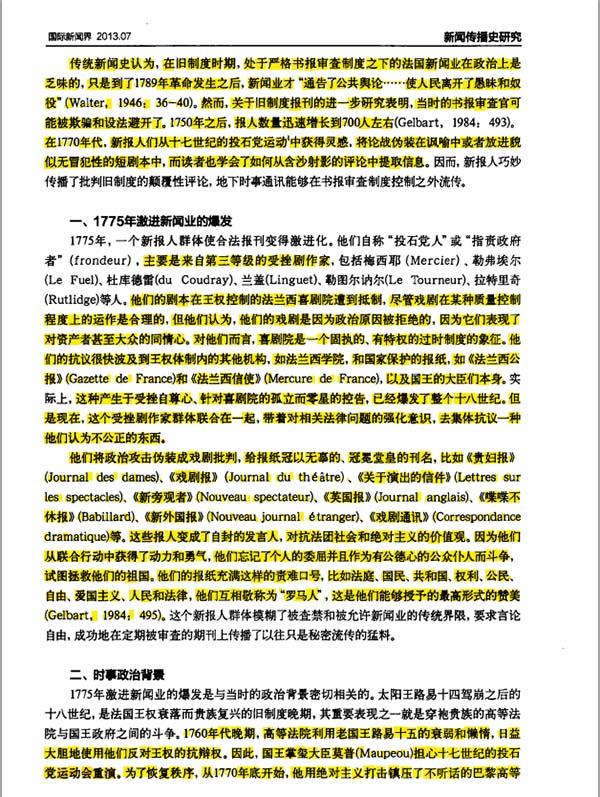韩二最近玩起了电影,一听到这个消息,吕某就下定决心,心想哪天不幸染上自虐症,想要自己恶心自己,宁可去看郭美美干露露芙蓉姐姐的视频,也不会看他的;宁可去看苍蝇下蛆蚊子交配,也不会看什么后会无期。
我是很对文化人总是心中佩服的,甚至是心怀敬仰的。当然我的文化人定义是非常苛刻的,并没有把理工科人士记入在内,毛主席曾经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主要还是理工科大学。这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文科人才尤其是作家政治家是很难通过学校去培养的,社会于文科人才来讲可能是最好的大学,人生磨砺可能是最好的老师,这就是为什么高尔基将他的人生三部曲中的一部叫做《我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人要比理工科人士要难成才得多的多,标准也复杂得多的多。
另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应当是情怀天下心系万代的,他们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笔下起风雷。大众的想法,在他们那里见诸文字;大众的情感,在他们那里得以抒发;大众的主张,由他们为之呐喊。他们具有大众的情怀,符合历史的方向,遵循道德的正义,服从科学的规律。由此看来,真正的文化人就应当是大众的,历史的,道德的,以及科学的。所以,我没有理由不佩服他们不景仰他们,那些真正的文化人。
因为这种敬仰是发自肺腑的,是真诚的,也就对那些以文人面貌出现的皱着眉头假作仰望天空状却时刻不忘自己的利益的名义上的什么普适价值的卫道士什么公共意见领袖实际是政坛戏子文坛小丑的痛恨,为一些同胞的愚昧和善良而上当受骗感到惋惜。
因为喜爱,平时也就留心文人尤其作家的成才之道,羡慕那些大器早成的神童,也敬佩那些自身条件和家庭条件并不是很优越最终却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作家。象刘绍棠,初中写的文章,编入了自己的高中课文里。北大上了一年,退学专职搞创作。同班同学谢冕日后成为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学者。我以为文学创作靠学院派有些牵强,文学评论的学院派还是靠谱的;象高玉宝,小时候没上过几天学,是从部队的扫盲班里走出的畅销书作家;象胡万春,我是从小人书《家庭问题》开始知道有这么一位作家,后来通过报纸刊物才知道是一位没上过几年学的童工出身。
有道是英雄不问出处,出现韩二这样的少年毕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联系到当今应试教育的弊端和千军万马独木桥的高考现状,这简直就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但是,当我看到这位天才的讲座,我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如同吃了苍蝇。
我接触作家的机会不多。所以,难得有一些作家的讲座我都是要去听一听的,不听觉得对不起人家也对不起主办方。当然,听过的不多,回忆起来有杨益言、胡万春、谭谈、刘宾雁,这些作家都是上学时有幸聆听的,现在网上的视频讲座访谈就不算在其中了。
就今天的话题而言,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老几位,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邀请的附近桃浦公社的一位年轻人,他是《一副保险带》最早的编剧之一,他给我们介绍了小戏的创作过程和电影的改编经过。很可惜,当初年少,没有记住人家的名字。毕竟业余作者,口才不是很好,但是表达流利,思路清晰。说口才不好,是和以后我听过的那些名作家相比,在语言的幽默风趣上稍有欠缺而已,其思想性和逻辑性是不逊于那些大家的。袁枚有诗云:苔花米粒小,也学牡丹开。一个作家的基本素养,无论大家还是小有成就的业余作者,都是必须具备的。
逻辑思辩能力对于从事文学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代文豪陈寅恪建国后到中山大学赴任挑选助手时提出的要求就是数学要好,他首要看重的是助手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不是文字功夫。文字功夫可以很快得到改进,而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是需要慢慢培养的,一个逻辑混乱的人不但写不好书评做不了考证,也创作不了好小说。试想,曹雪芹如果逻辑混乱的话,如何在《红楼梦》里处处埋下条条伏线让一代又一代的红学家们索引考据乐此不疲?
有人总喜欢拿田汉钱钟书说事,好像他们是因为学不好数学才转学文学的。这里有误会,我以为,他们那个时代新学乍起,理科包括数学教师稀缺而已。并不是他们没有学好数学的能力,而是没有学习数学的机会。被周总理称为“三钱”之一的钱伟长考清华的时候,数学不及格,作文和历史满分。直到晚年接受央视《大家》栏目访谈时他还为自己的作文自豪,说阅卷老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动。当然,现在更值得他自豪的而且值得全体国人为之骄傲的是他在数学力学上的贡献。
所以,我的观点是,作为一个作家,作品缺少思想性,就不是一个好作家;如果不具备起码的逻辑思维能力,根本不能成其为作家。
韩二所处的年代已经和上世纪初的田汉钱钟书所生活的时代大不相同,他也不是生活在闭塞的偏远山村,他在理科方面的能力欠缺已经不能用时代的和地域的局限来为他开脱。他应易中天先生的邀请在厦门大学所作的所谓演讲则让我对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不得不进行怀疑。看过视频之后,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在无产阶级大革文化命的流氓加文盲时代的我的中学同学在批斗会上念的发言稿都比他的这个演讲要强。
面对这个视频,面对如此天才神童,我咬住了仇咬住了恨,咬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中华民族的神童就算现今都死绝了的话,历史上的周瑜谢缙骆宾王离我们远去的话,那郭沫若刘绍棠并没有远去,那温家宝还能活蹦乱跳地跳绳打篮球,怎么就单单选上韩二?全国人民瞎了眼?我皱眉蹙眼望夜空,但见满天星,就是想不通。
我不怪韩二,看那三寸丁不男不女,想起那句话丑八怪也自认为是天仙女,孔子的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矣用在韩二一人身上,用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话说,那是姓何的嫁给姓郑的——正合适(郑何氏);也不怪韩大,有其父必有其子,用独角戏大师周柏春的话说,就是癞痢头的儿子也是自家的好。再说,革命传统代代传,那点本事不传韩二,难道传易中天不成?
我看不上易中天,韩二年龄小你也小?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他要不是东西你也跟着不是东西?外国人说他是意见领袖,你就信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那里去了?文化人的人文情怀又哪里去了?让韩二做你的意见领袖,让他念着讲稿说话还不利索去启发你的新思维,是你的大脑掉进了大肠还是你的大肠填满了大脑?
前两年吧,网上的视频,标题是“易中天节目现场发飚,气哭两位主持人”。一个年逾花甲的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对年轻的主持人不理会,不合作,出言不逊。既然有不愿意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又何必上人家的节目呢?
我必须说明,我是易中天先生的粉丝,曾经是,今后还没打算不是,但粉丝并不就意味着全盘接受。他的电视节目和讲座我都是必看的,《品三国》我是一集不落地看完的,有的还看了几遍。他的中国封建社会三段论和我中学时评法批儒运动中接受的观点还是吻合的,这说明他站在右派的立场上还是具有左派观点的,至少说明他还没有右到完全迷失自我的程度。
我也看不惯许多节目中主持人的浅薄与无聊,也反感他们的八卦和低俗。但是,视频中的两位主持人就当天的表现离上面的负面因素还是想去甚远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两位主持人再不靠谱也比韩二强吧,至少人家没有翻着白眼拿着稿子舌头打着结去念吧。易中天既然有无颜面对两位年轻主持的勇气,又何来屈尊邀请韩二来厦大讲学的脸皮?易中天能够气哭两位主持人,说明人家还有羞耻心。方舟子的话不可谓不重,却从未气哭过韩二。
易中天在《开讲啦》里面是这样回答学生对他的《易中天中华史》里有关嫦娥的描述的提问的:我坚信一条,当一个作家只有当你自己写爽了的时候,你的读者才会爽。一个36卷本《中华史》,居然只用五到八年就可以写完,做出这样的决定不知道需要怎样的学术精神?如果真的能够在五到八年内写完,又需要怎样的学术勇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一再承诺要将下半卷付梓,却始终是一本上卷书,害得有人拿大师打镲叫胡适为胡公公,说他有了上面缺了下面。
易老师有激情,但希望不要把做学问当成做爱,图个爽字;也不要将交朋友当成找小姐象韩二那样的,年轻无脑的。我这么说,不是说我有多么猥琐,而是实在想不通易老师的三角眼怎么单单就瞄上了韩二?如同广电部居然就将电影拍摄许可证给了韩二?
刘宝瑞先生有一个经典单口作品《连升三级》,说的是明代天启年间,纨绔子弟张好古,是个大文盲,官迷心窍,竟异想天开,进京赶考。由于皇帝和文武大臣的昏庸腐败、尔虞我诈,使张好古钻了空子,居然金榜题名,进了翰林院,并且阴差阳错,连升三级。我真不希望刘宝瑞作品里的张好古在今天复活,借尸还魂。
如果韩二有真才实学的话,还其清白。如果确实属于欺世盗名的话,还是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昭示世人当今时代,虽市场经济商品社会,张好古之流是绝无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