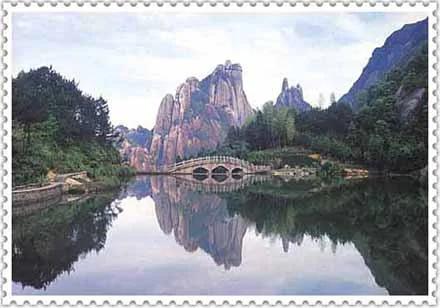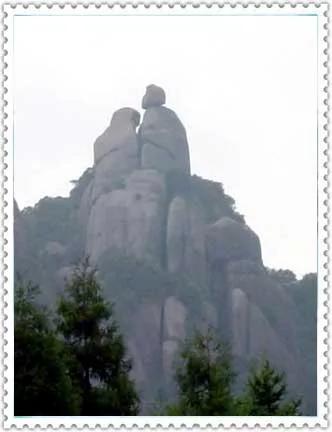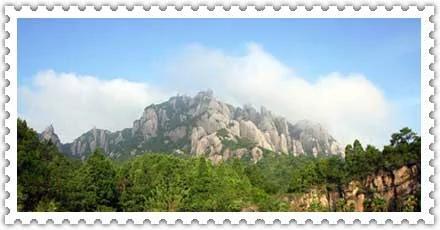1907年七月15日是鑒湖女俠——秋瑾罹難的日子,時至今日,距秋瑾慷慨赴難已是足足百年,百年前風雨如晦的中華大地上,三十一歲的秋瑾倒在了魯迅筆下的"古軒亭口"。曾經的壯懷激烈、曾經的悲怆滿懷,依然萦繞在衆多國人的胸懷,"古軒亭口"的殺戮依舊是我們心頭難以忘卻的那一抹傷痛!
富與貴、官與商,在綿延而輝煌的中國曆史上,向來都是比翼鳥、連理枝,難分難舍。秋瑾出身于高幹世家,自幼學文兼習武,其父秋壽南爲湘潭厘金局總辦,财權在握,錦瑟華年的秋瑾也很自然的嫁入了豪門,新郎是湘潭巨富王二胖子的獨子、曾國藩的表侄王廷均。雖然王廷均隻是一典型的纨绔子弟,但作爲才女又不乏名利的秋瑾,完全可以像李清照一樣,寫詩作畫、雕弄古玩,頂多面對同樣的山河破碎,發幾句哀歎、寫幾首愁詩,然而俠女兼才女的秋瑾必竟不是李清照。利錐終将刺破頑麻、蒼鷹也終将騰向浩瀚的長空,1904年初秋瑾變賣了自己的妝奁首飾,破蛹化蝶般的奔向了革命黨人的集聚地——日本而留學。
赴日求知前後的秋瑾,可謂判若兩人。久在深閨時孤高自傲,自然多了些無處覓知音的凄愁,"容易東籬菊綻黃,卻教風雨誤重陽。無端身世茫茫感,獨上高樓一舉觞"(《重陽志感》),而八國聯軍的入京、四萬萬兩的賠款,逐漸使秋瑾的滿腔憂憤溢于筆端,"幽燕烽火幾時收?聞道中洋戰未休。漆室空懷憂國恨,難将巾帼易兜鍪!"(《杞人憂》)。她有時憂憤的又兼有點無奈,"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滿江紅?小住京華》)。1903年秋瑾讀到了一些提倡民主革命的報刊雜志從而決定赴日本留學,1904臨行時她仿佛看到了一絲曙光,"鐵畫銀鈎兩行字,岐言無限叮咛。相逢異日可能憑?河梁攜手處,千裏暮雲橫。"(《臨江仙?回贈友人》)。在日本,秋瑾與革命黨人劉道一等人組織"十愛會"以圖恢複中華,不久又參加秘密反清會黨洪門天地會,受封爲"白紙扇",她在東京倡辦《白話報》鼓吹革命并四處演講,年底回國後結識了蔡元培,并經徐錫麟介紹加入了光複會。在日本一年的經曆大大拓寬了其視野與胸襟,革命的火焰已在心口跳躍,第二年再返日本的途中,其詩詞手筆是如此的大氣而沉重:"萬裏乘風去複來,隻身東海挾春雷。忍看圖畫移顔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拼将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黃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見日碚稭赝肌罰G镨菩私樯苡朐谌氈鏡乃镏猩交嵛睿⒓尤肓送嘶幔煌蒲∥?/FONT>浙江省主盟人。茫茫海外,秋瑾與這群壯志豪情的熱血汗子一起,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祖國沉淪感不禁,閑來海外覓知音。金瓯已缺終須補,爲國犧牲敢惜身?嗟險阻,歎飄零,關山萬裏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鹧鸪天?祖國沉淪感不禁》)。其豪氣萬丈的詩章"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對酒》),一度被譽爲明清豪放詩詞的巅峰之作。回國後秋瑾一直爲革命事業四處奔走,1907年接任大通學堂督辦後,遂以大通學堂爲中心聯絡會黨,并常身着男裝、腰藏倭刀、跨着駿馬,英姿飒飒的訓練軍隊。
中國的曆史,大都是帝王将相的花名冊,偶有一些常稱爲史筆留芳的才女、美女、貞女、烈女、俠女等點綴其中。才女,如李清照、張愛玲等,男人們除了傾歎、就是憐惜,能以纖纖玉指、隽秀手筆訴說出無盡的相思與柔情,賞心處如仙肌拂面、如禅房花香;傷心處則字字帶血、則如泣如訴,吾等粗蠻之人甚至不敢有謀容之念。美女則不同了,男人們紊亂的大腦中常隐現着意淫的火花,恨不得于茫茫人海或時空隧道中與其刻意相逢,然後極力展示自己的才能或富貴,并頌美女之芳華、哀美女之不幸,高談處啧啧有聲,低思時噓唏不已。一代名妓蘇小小甚至有不少文人到其墳頭放聲痛哭,傳說中的絕頂美人王昭君,後世連其畫像都未見過的文人,爲其寫的詩詞竟高達幾萬首,位居中國詠人之詩詞冠首。貞女烈女等傳記是寫給自家女人看的,她們以柔弱的肩膀甚至卑微的 生命,換來了一座座滿足男權私念但飽含血淚的牌坊。俠女大都隻是傳說,史上略有記載的戎裝擊鼓的梁紅玉,便已讓千百男兒精神一振,至于所謂的代父從軍的花木蘭、風塵狂野的紅拂女、橫掃千軍的穆桂英、骁勇善戰的洪宣嬌等,小說家言,姑妄聽之。縱觀幾千年曆史,能同時做到劍舞龍蛇、豪氣萬丈、運籌帷幄、文才絕代而又敢于挺身赴難的奇女子,隻有秋瑾一人。
1907年7月6日,"隻解沙場爲國死,何須馬革裹屍還"的徐錫麟在安慶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而恩銘則是慶親王奕劻的女婿、浙江巡撫壽山的連襟、慈禧太後眼中的國家棟梁。恩銘遇刺一案舉國轟動,慈禧太後也痛哭不已,在下令對徐錫麟剖髒剜心的同時,還要求嚴加追捕、徹查此案,很快便牽連到大通學堂。消息傳來,衆人皆勸秋瑾暫避,秋瑾卻僅僅疏散學生、銷毀名冊,已抱定了流血犧牲的決心。7月13日清兵圍攻大通學堂,激戰後終捕獲秋瑾。
曆史這東西,猶如婊子的牌坊,功過榮辱,弄權者皆可操刀簡筆,任由奸之。我隻覺得:世間萬事,盡在公心,而公者,民也。虛構中"爲國爲民、俠之大者"的郭靖率襄陽軍民螳臂當車似的抵擋着蒙古的鐵騎,史載裏屈身安民、俸事五朝的馮道屢次率衆臣安順的迎接新王朝的軍隊,但他們都是我所尊敬的人。同理,在風雨飄搖的南宋偏安小王朝,主和的秦桧是漢奸,主戰的韓佗胄也不是什麽良臣。筆者的眼中看到了一名火熱豪情的女子,面對着山河破碎、強敵眈眈,毅然放棄了仕宦富貴,如俠士般的四處奔走、慷慨呐喊而最終選擇的是與譚嗣同比肩的豪舉:去留肝膽兩昆侖。經過兩夜一日的突審加用刑,紹興知府貴福最終隻得僞造供詞、強捺指印,并于1907年7月15日在紹興的"古軒亭口"将秋瑾暴屍于衆,而秋瑾留于世間的最後手迹,隻是引自清代詩人陶淡人《秋暮遺懷》中的一句"秋雨秋風愁煞人"!好一個愁煞人,如今,百年已過,中華大地依舊滿目瘡痍、體無完膚,怎奈不愁煞人也!
"中原亂,簪纓散,幾時收?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這是南宋詞人朱敦儒經過金陵時的沉痛獨白,筆者無從得知秋瑾被押向古軒亭口的路上是不是腳步異樣的沉重,不知道秋瑾幾年的奔走是不是也會常想起年幼的單子孤女,不知道秋瑾對這首蒼涼悲憤的詩詞會不會心有戚戚,或許在這位奇女子的眼中,僅僅是執着、僅僅是坦然,然而百年的風雨掩飾不去的,是我們分明感受到的那種滿腔的豪邁與悲壯。
一直很難想象秋瑾她那纖弱的雙肩如何扛得起革命二字的悲怆與沉重。我們無法得以親睹鑒湖女俠的芳容,唯有在自己的大腦裏描繪她的顔容了。我看過西湖邊的秋瑾墓,墓旁的秋瑾雕像綽約而冷竣,而當經過紹興的古軒亭口時,那裏已是商賈彙集、人頭攢動。順手翻開史書上的秋瑾像,那是一名很清秀的女子,隻是與其他女子不同的是,其兩眼如刀。其實對女人來說,風情萬種、柔情似水、狂野灑脫、靜秀端莊等都是一種美,隻是相比于這些而言,秋瑾的這種兩眼如刀才是最給人一種震撼的驚豔和别具一格的魅力。
百年已飄逝而過,塵世依舊,除了雕像與紀念館,世間還給秋瑾留下了些什麽?如今,百年前的雲海仍然翻騰、風雷依舊激蕩,隻是國人更爲物欲而繁忙,這是一個出國留學已變味爲高幹子弟替父母洗錢的時代,這是一個漫天廣告下老老少少都在熱衷于滋陰壯陽的時代,這是一個少男少女對古時的優伶歌妓即現在所謂的影星歌星竟然頂禮崇拜且趨之若鹜的時代,這更是一個官官商商都在忙着愛權愛錢卻将國家寄望于他人來愛的時代。這個時代中,美女泛濫,特權泛濫更甚,因而整個社會也更凸顯出與衆不同的"熱鬧非凡"。太多的人即使擠破了腦袋也要鑽進權力的褲裆裏去;有人極端自戀的總認爲自己才貌都是出類拔萃,有人在征婚中拖着長長尖尖的聲調說"沒車沒房的男人滾";有人借助着網絡以身體的大膽出位而謀求一夜成名,還有人自認在性交易中吃了虧而叫喊着要以無恥來對抗無恥。放眼望去,烏煙瘴氣的中華大地,一群庸脂俗粉,在上竄下跳、醜态頻頻。
秋瑾女俠曾經賦詩曰:"孤山林下三千樹,耐得寒霜是此枝"(《梅》),或許,這是她給自己的内心素描。百年後的今天,作爲塵世一栗的我,不能于月缺之夜攜酒到其墓頭去高歌"浩浩愁 ,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而唯有以愚鈍之筆,作些無關痛癢之辭,不知鑒湖女俠之泉下魂靈,是否依然兩眼如刀......